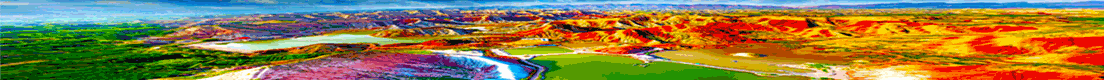《枯樹賦》是北周詩人庾信暮年所作,反映出對當時社會動亂的心有余悸,感傷遭遇。最后一句是千古名言:“昔年種柳,依依漢南;今看搖落,凄愴江潭。樹猶如此,人何以堪!”褚遂良為初唐楷書四大家之一,承前啟后,學歐虞而能自化,影響了其后的李邕和顏真卿。褚遂良在唐楷中融合了隸書的古意和“二王”行書筆意,端莊凝重中見靈動飄逸,歐虞以來的嚴謹面目為之一變。
唐貞觀四年十月八日,35歲的褚遂良為時為權貴的燕國公抄寫庾信《枯樹賦》,共39行,476字。當時褚遂良只是個起居郎官,尚無書名,不知何故會專為燕國公作書?而且這篇抄寫之作,竟使燕國公珍為寶藏,以致流傳后世,成為其行書代表作。
從整個唐代書法史來看,褚遂良《枯樹賦》與虞世南《汝南公主墓志》和歐陽詢《卜奠帖》,處于同一水平和地位。
《枯樹賦》全為《蘭亭》筆意,有魏晉風度,其中的“苦、集、臨、風、月、吟、文、蹙”等字,可以與神龍本《蘭亭》相比。筆觸輕松,靈動多變,多見空中行筆,結構舒朗蕭散,筆畫瘦硬,結體少見唐人專尚結構的習氣,殊為難得,堪稱臨學經典范本。對于《枯樹賦帖》,宋代陳藻跋贊“褚登善書用隸法”,明王世貞稱“掩映斐疊,相有好致”,明周天球言“整密秀潤”,謂之“風流儒雅”,可能最為形象,字字靈秀,宛若翩翩君子。
翁同龢早年從習歐、楮、柳、趙,書法崇尚瘦勁,中年轉學顏體,取其渾厚,又兼學蘇軾、米芾,書出新意;晚年得力于北碑,平淡中見精神。一生博采眾長,對唐代顏真卿和北魏碑版潛心揣摩,參以己意,并吸收劉墉、錢灃、何紹基等人之長,將趙子昂、董其昌的柔和流暢溶入其中,習顏而出已意之法,用筆奇肆率意,結體寬博開張,風格淳厚大氣。
清徐珂《清稗類鈔》謂:“叔平相國書法不拘一格,為乾嘉以后一人……晚年造詣實遠出覃溪(翁方綱)、南園(錢灃)之上。論國朝書家,劉石庵外,當無其匹,非過論也。光緒戊戌以后,靜居禪悅,無意求工,而超逸更甚。”馬宗霍《霎岳樓筆談》贊:“松禪早歲由思白以窺襄陽;中年由南園以窺魯公;歸田以后,縱意所適,不受羈縛,然氣息淳厚,堂宇寬博,要以得魯公者為多。偶作八分,雖未入古,亦能遠俗。”
從筆意方面來說,前后自然連貫,較為從容,不存在茍且之筆,筆墨暈化,特別有層次感,筆畫粗細對比強烈。看來翁同龢對于《枯樹賦》不止一次地臨摹過,后來也確實找到了兩件臨作。三件皆為節臨,心態、狀態和情態各不相同,這是一個書家應變能力的體現。
顏字的成分更多一些,整體上更加嚴謹端莊,乃翁同龢慣常風格,名曰臨,實為自寫胸臆。
多了些米芾的筆法,更加老辣蒼茫,不拘繩墨。三件各見風致。
在現實中,很多書家卻做不到這一點,在不同情況下臨摹同一種碑帖,常常陷于一種“模式”,無疑很容易固化。翁同龢雖言學顏,得其雄放之姿,而舍其筆畫厚重之形,融入米芾筆意,雖然紙面有界欄,但是行筆不為所拘。筆力沉郁,氣度恢宏,縱橫捭闔,別具雍容肅穆之致。翁氏晚年曾說“寫大字,始悟萬法不離回腕納懷,此外皆歧途。”以臨為創,或者說,已經不是單純的臨摹,只是借助這一段內容,做到意與古會。臨摹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必然行為,但必然要求中有一些偶得,兩者決定了臨摹的最終效果。
翁同龢(1830-1904),先后為同治、光緒兩代帝師,歷官刑、工、戶部尚書,協辦大學士,軍機大臣,總理各國事務大臣等。翁同龢為清代書法大家,一生以顏真卿為范,融入米芾筆意,凝重中見瀟灑之意。
●小貼士
1、建議選用兼毫“七紫三羊”,更能表現筆畫勁健的風格特點,加上濃墨,顯得精神抖擻。
2、褚遂良和顏真卿雖然看起來風格差異巨大,實際上有內在關聯,顏是學褚的,早期學得很像。學書法不但要了解某個書家成熟期風格特征,也要了解彼此之間的關系,以及一個書家的前后期發展脈絡。
3.書家風格一旦走向成熟,臨摹起來就自動尋找自己所想要的,從而在風格上不拘于原帖,貌離神合。但一件碑帖如果反復臨,一定要注重臨摹出不同的感覺,做到一時有一時之態,而不是簡單地抄帖,要努力把個人不同的感覺最大可能地發掘出來。
據《北京晚報》